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摘要:我国《公司法》第182条所规定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是将强制解散公司定位为少数股东的最后救济手段。但解散公司并不能彻底救济小股东,也无法打破公司僵局,在很多情况下公司僵局从解散阶段延续到了清算阶段,导致公司无法清算注销。同时,公司僵局往往伴随着股东压制,造成僵局中的弱势股东被锁定在封闭公司中持续受到压迫。本文以功能主义比较为研究方法,回溯英美国家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改革历史与演变趋势,发现经过上百年的发展,英美公司法发展出多种股东救济手段,以打破公司僵局,其中最为常用的为股权强制收购。在我国《公司法》修改之际增加股权收购请求权符合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进化规律,过往司法实践中股权收购调解的尝试也证明此种救济方式具有本土可行性。故此,我国《公司法》可以借鉴英国法对公司解散与股东压制分别救济的立法模式,在《公司法》第十章第182条针对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与第三章第74条针对股东压制的救济制度中分别增设或完善作为救济方式的股权收购请求权。
关键词:司法解散 公司僵局 股东压制 股权收购请求权 决斗机制
一、最高人民法院8号指导案例的回溯与跟踪
2012年4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下文简称最高院)发布第二批指导性案例,其中第8号指导性案例——林方清诉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戴小明公司解散纠纷案(下文简称林方清案),从个案的角度对《公司法》第182条“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进行了限缩性解释,即不再综合考虑公司的经营和管理是否发生严重困难,而是侧重于公司的组织机构运行状况,公司是否经营亏损并非构成公司经营管理发生严重困难的必要条件。[1]8号指导性案例在实践中具有了参照适用的功能,极大提高了法院判决解散正常营业公司的比例。[2]然而凯莱公司在判决解散后仍“原封不动”地正常经营,引发学界对该案的反复讨论,是具有争议性的典型案例。本文尝试从该案判决书中的细节着手,并对凯莱公司在判决解散后进行跟踪式研究,反思该案的社会效果及我国司法解散制度的不足。
(一)隐藏在公司僵局中的股东压制
凯莱公司为某服装城产权所有人,主要从事商铺出租。公司的两位夫妻股东林方清与戴小明[3]各占50%的股权,并且公司章程规定股东会决议须经代表二分之一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股权比例和章程规定直接导致一旦双方有矛盾,股东会就无法作出有效决议。此外,双方约定戴小明为执行董事,负责公司的日常经营,林方清为执行监事,对执行董事进行监督。由于夫妻双方关系破裂甚至发生肢体冲突,直接导致股东会无法召开或不能形成有效决议,且戴小明多次拒绝林方清查询公司财务资料的要求。但公司仍在戴小明的控制下继续经营且处于盈利状态。此时公司的权力机关瘫痪,但业务执机关仍在运转。林方清案的特殊之处在于,不仅在公司层面造成僵局,还在股东内部关系上具有控制人的压迫。林方清虽为持有50%股权的股东和执行监事,但公司长期不召开股东会,林方清无法通过行使表决权来参与公司决策,其关于查询财务资料的要求也一再遭到拒绝,正如二审法官在判决书中说的那样,林方清的股东权、监事权长期处于被剥夺的状态。[4]而法官在作出解散判决时,只考虑了公司内部管理严重障碍,没有考虑股东压制的情节,忽视了对弱势股东的保护。
(二)作为谈判筹码的解散判决
凯莱公司在被最高院驳回再审请求后并没有解散,双方股东在强制清算过程中达成了和解协议:对凯莱女装写字楼按照各50%股权比例进行实物分割,分割至两股东各自注册设立的公司名下,各自成立分公司经营管理。嗣后双方对凯莱女装写字楼的分割划定了红线图。经现场抓阄,林方清取得写字楼东半部分的经营权,戴小明取得西半部分的经营权。并由清算组告知写字楼的所有承租户,要求承租户各自与林方清和戴小明分别联系,分别订立租赁合同、交纳租金。但是,戴小明并没有按照承诺履行和解协议,未将林方清分得的写字楼一半产权过户到其注册的公司名下,导致林方清只能以自然人的名义与租户订立合同。名义上,双方各自经营、自负盈亏;但在法律上,双方的股东身份并无变化,戴小明仍是凯莱公司的法定代理人,从而造成了公司经营事实与法律的错位。林方清虽为法律意义上的股东,但在和解协议分别经营的约定下,被排挤在公司经营管理之外,后多次提起股东知情权之诉,要求了解公司的财务状况,但法院以和解协议的分别经营为由驳回其请求。[5]双方的矛盾还进一步影响了租户对商铺的正常使用,林方清将位于写字楼公共区域的商铺出租给租户梁莎莎,戴小明则根据和解协议约定的公共区域管理权,以消防安全为由对该区域断水断电,导致梁莎莎无法使用商铺。[6]
国内学者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法院即使判决解散盈利公司解散,股东在私底下还是会通过谈判避免公司走向清算注销,解散公司判决书只是给了原告股东讨价还价的筹码而已。[7]但在本案中,林方清作为被压制的弱势股东并没有在拥有了解散判决这一筹码后在博弈中胜出,反而双方的矛盾积年累月宿怨加深,变得更复杂更加难以调和,由此造成经年的诉讼也为司法机关增加了讼累。通过林方清案可以看到,通过强制解散为弱势股东增加的谈判筹码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博弈格局,并不能解决股东之间的矛盾,而僵局中的弱势股东有可能仍会被锁定在公司中同时持续受到压制。[8]在公司法没有授权法官其他救济方式的情况下,法官只能在拒绝救济与判决解散之间艰难的二选一。[9]
二、英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历史演变与启示借鉴
公司司法解散是2005年《公司法》修订新增的制度,相比英美国家确立较晚,尚不完备。通过梳理英美两国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演变,可以帮助我们在百年的时间坐标下,认识该制度的历史演变规律,把握公司解散制度的变革方向。在此基础上比较两国司法解散不同的立法模式,分析不同模式的利弊,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逻辑与体系逻辑。
(一)英美司法解散制度的演化史
英国是现代公司制度的发源地,司法解散制度正是诞生于十九世纪的英国。最早英国公司法授权法院在公司发生分歧和僵局时对公司进行清算。直到1947年,股东针对公司控制人的压制行为唯一救济途径仅有公平和公正的清盘(just and equitable winding-up)。[10]当时的英国法官认为清盘是非常激烈的救济方式,很少作出清盘判决。在英国公司法修订委员会建议下,1948年《英国公司法》第210条规定增加了授权法官调整公司事务的处理方式、要求公司或其他股东购买股份为公司清盘的替代性救济措施。即便救济方式的范围更大了,但第210条要求必须要满足股东压制才能获得救济。而当时法院股东压制的解释非常严格,压制行为必须是“繁重、苛酷和错误”(burdensome, harsh and wrongful)的。[11]而且,相关行为必须是针对原告作为公司股东的压迫,而不是对作为董事、公司雇员的压迫。[12]最后,该行为必须是在一段时期内持续或重复发生,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个别行为。法院的狭隘解释导致少数股东很难获得救济,随后1980年《英国公司法》以不正当损害(unfair prejudice)替代股东压制(oppression),意在为法官判决提供更大的灵活性。此外,在救济方式上授权法院做出其认为合适的命令,并举例说明了法院可能做出的命令类型,包括要求公司或公司成员购买其他成员的股份等,这一修改也标志着清盘法定替代性救济的形成。[13]1986年《英国破产法》增加公司解散规则,对破产做了扩大解释,不仅适用于资不抵债的公司,还适用于公司自愿解散和强制解散的情形。[14]由此,破产法替代了公司法中的相关规定,随后的公司法修订删去了重复部分。
而传统美国法授权法院灵活多样的强制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方式,允许法官在运用衡平权力自由选择,但是由于这些衡平救济手段都规定在“司法解散”的框架之下,[15]即公司只有满足了司法解散的条件,股东才能获得其他方式的救济。[16]以解散事由作为其他救济方式的衡量标准造成许多法院采取过强的限制性立场——除非法院确信解散是合理的,否则不能给予任何形式的救济。为阻止强制解散成为法院唯一依赖的救济方式,1984年《美国示范公司法》增加了第14.34节,在司法解散中创设了股权购买选择权(Election to Purchase In Lieu of Dissolution),公司或剩余股东可以选择购买原告股东的股权,替代司法强制解散。[17]
回溯英美两国司法解散制度的演化历史可以发现,司法解散制度从一开始就被作为公司内部矛盾的解决机制,并承担了保护少数股东的功能。与此同时,英美法官都认为公司解散是一种极其严厉的措施,对其采用严格限制性立场。经过数年的修订和改革,立法发展出了多种替代性救济措施,将强制解散定位为对股东的最后救济。相比之下,我国公司法尚停留在以解散公司来保护少数股东的立法阶段,没有在规范层面规定公司僵局的替代性救济,公司法司法解释二中的调解成了解散公司之外唯一的司法救济。从司法解散制度的变革趋势来看,增加替代性救济方式是我国公司法亟需完善的部分。
下文将具体介绍现行英美两国公司司法解散的立法体系、法定事由、救济方式,在比较差异的基础上分析不同模式的利弊。
(二)英美立法模式的差异
1. 英国模式:公司解散与不公平损害的分别规制路径
如上文所述,英国立法者将公司解散制度从公司法移到了破产法中。1986年《英国破产法》第四部分规定了公司的解散,具体包括成员自愿解散、债权人自愿解散、法院决定的解散,以及解散后对公司的清算和注销程序。根据《英国破产法》第125条,股东有权通过解散寻求救济,在没有任何其他救济方式的情况下,公司解散将被视为公平和公正的。而对股东的其他救济方式主要集中在公司法中的不公平损害诉讼。2006年《英国公司法》第994条规定了股东有权以不公平损害、侵害股东利益为由提起诉讼,请求法院救济。[18]法院在审查股东利益时,通常会从合理期待(legitimate expectations)来判断,即股东对公司事务以一种合理期待的方式作出,如果不能以这种期待的方式运营公司,就构成对该股东利益的不公平损害。[19]第996条还规定了法院在不公平损害诉讼中可以作出的五种救济令:(1)调整公司将来事务,如对董事的任免、召集会议等;(2)要求公司作出或停止特定事项,如要求公司支付红利或制止公司对董事支付过高的薪酬等;(3)允许原告以公司的名义、代表公司提起民事诉讼;(4)未经法院同意,公司不得对章程作出任何修改;(5)要求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自己购买任何股东的股份,对于公司自己购买,据此减少公司资本。
2. 美国模式:司法解散制度下的分层救济
《美国示范公司法》[20]第14.30节规定了股东请求司法解散的四种事由[21]:(1)董事在经营管理公司事务时产生僵局,且股东无法打破僵局,公司有可能遭受或正在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2)控制股东或董事的非法、压迫或欺诈性行为;(3)股东在表决权上陷入僵局,且至少连续两次年会期间未能选出任期届满的董事的继任者;(4)公司资产被滥用或浪费。[22]其中(1)(3)属于公司僵局,包括董事僵局与股东僵局,(2)(4)属于控制股东或董事的压制行为或权力滥用。前者是对公司陷入瘫痪的客观状态描述,没有表明任何一方应对僵局的形成负责或负有过错;后者强调对个别股东利益的损害。[23]可见,美国采取的是统一适用司法解散制度救济公司僵局和股东压制。在对压制行为的判断上,法院同样适用“合理期待”(reasonable expectations)作为压制行为的界定标准,如果公司的决策违反了股东投资时的合理期待,即便是在公司法规定在权限范围内作出的,也构成压制。[24]
2016年修订的《示范公司法》在原有的规定上增加了适用司法解散的公司类型,将上市公司和股东超过300名、市值超过2000万美元的非上市公司排除在外。[25]在解散之诉中,公司或其他股东可以选择以公允价格购买起诉股东的全部股权,以终止解散程序。股份购买选择可以在原告起诉后的90日内向法院提交,一经作出,不得撤回。双方可以就股权价格进行协商,如无法达成一致,法院可以应任意一方当事人的申请中止股权收购程序,或按照起诉的前一日或其他适合日期确定股票的公允价值。[26]美国的股份买断本质上是自愿购买,由原告之外的其他股东自愿选择,在价格无法达成一致时也可以中止。
除此之外,针对封闭公司的人合性,《美国封闭公司示范附加规定》规定了法院的分层救济方案(tiered remedial scheme),[27]依次为普通救济,[28]特别救济之股权购买,特别救济之司法解散。[29]司法解散作为最后救济方式,只有在其他救济都未能解决争议事项时才得以适用。
《美国示范公司法》虽不具备成文法的效力,但为美国各州制定公司法提供了参照的范本。根据美国学者的整理,有32个州直接采用了《示范公司法》中的司法解散制度,39个州规定了股权买断作为公司解散的替代性救济措施,[30]14个州没有将股东压迫作为解散的法定情形。[31]
(三)两种模式的利弊分析
1. 司法解散制度的不同体系
英国立法者认为公司解散与破产同属于市场退出机制,故由破产法来调整公司解散,由公司法来调整对少数股东的不公平损害,并确定了不同的认定标准,前者从公司的整体利益考察,后者从股东合理期待是否落空来判断。二者的交叉之处在于,如果“不公平损害救济”无法解决争议,股东可以提起公司解散之诉;而在司法解散中,法官也可以作出股份购买等替代性救济措施。这种交叉管辖可能使问题复杂化,造成一个案件提出两种申请的不合常规做法。英国法律委员会曾建议整合诉讼程序,在不公平损害中,把停业清算增加到法院可采取的救济措施清单中。[32]但反对意见(贸易工业部)认为,在“不公平损害”[33]和“公平公正的清算”[34]中分别规定公司清盘会导致不同的认定标准,并且容易被滥用和作为股东施压手段。经过权衡,公司法审议指导组出于限制公司解散的考虑,没有将清盘增加到不公平损害的救济方式中。
与英国法不同,美国法采用的是独立的司法解散模式,完整规定了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程序、替代性救济措施,并且将股东压制列为公司解散的法定事由,司法解散制度同时承担了为少数股东提供救济的功能。
本文认为,公司解散与股东压制有着不同的制度功能与判断标准,将二者规定在同一个制度中会造成法律逻辑的混乱。公司解散立足于公司整体利益,而股东压制以少数股东保护为出发点。因此,英国法的分别规制是一种更为理想化的立法模式。
2. 股权收购主体
从提出股权收购的主体上看,《英国公司法》第996条“公司其他股东或公司自己购买任何股东的股份”的规定,既可以是公司或者剩余股东购买原告股东的股权,也可以是原告股东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在英国的司法实践中,法院判决原告出售股份与判决被告出售股份的比例为7:2。[35]
相比之下,美国法官就没有那么大的自由裁量权了。《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规定股份购买的选择只能由公司或原告之外的其他股东作出,因此提起司法解散的原告股东无权购买其他股东的股权,这就导致原告只能选择退出公司,而无法通过收购股权把对方赶出公司。尤其是在股东各持50%股权的两人公司,很容易造成没有任何一方愿意提起诉讼,从而被动同意成为股份出卖方。[36]这也导致了决斗机制(shootout mechanism)[37]成为了美国封闭公司非常流行的僵局解决方式,常常被写入公司章程或股东治理协议,并被美国律师协会写入《示范房地产开发经营协议》,成为房地产领域的示范条款。[38]这种类似于分蛋糕规则的“我切,你选”,由一方股东报价,另一方选择购买对方股份或全部出售自己的股份,有效弥补了成文法单方买断权的不足,双方能够享有平等的机会选择留在公司或退出公司。[39]由于这一机制在确定股权公允价格上的独特优势,也慢慢开始在司法环境中被运用,法官在双方股东都主张股权收购的公司僵局中,利用决斗机制决定股权的收购方和收购价格。[40]由于报价方可能会被迫高溢价收购或折价出售,他们有足够的动力确定一个尽可能公平的要约价格,正如美国第七巡回法院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法官在判词中所陈述的,“确定价格的人被迫收购或购买,这种可能性能够让出价者保持诚实”。[41]
三、中国公司司法解散的体系构建
(一)中国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路径选择
英国公司法与破产法分别规制路径虽然是一种更为理想化的立法模式,但并不适合中国。2005年《公司法》对“公司解散和清算”进行了专章规定,形成了公司“从生到死”的完整结构。如果删去这一部分,会造成公司法内生结构不完整,同时分开规定也会存在如英国法律委员会所说的双重救济问题。但是,我们仍可以借鉴英国法将公司解散与股东压制分别救济的思路,在一部公司法的不同章节里分别规定针对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救济与针对股东压制的救济,这样既可以保持法律逻辑的清晰,也可以兼顾公司法的体系完整性。
有学者提出将股东压制列为司法解散的法定事由,[42]且《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和大部分州法都是整合救济模式。[43]本文认为,分别规定是一种更好的立法路径。首先,在股东压制的语境下,司法介入是为了保护少数股东的权利,包括参与公司经营管理、利润分配等;而司法解散关涉到包括雇员、债权人在内的公司整体利益,需要考量的因素不仅是对少数股东的保护,两者的制度价值存在本质上的差别。此外,二者的认定标准也不相同,股东压制往往是对控制股东的单个行为进行认定,而在司法解散之诉中,法院会全面审查一段时期内公司的总体行为方式,而不是某些孤立的具体行为,以此判断公司的人合性基础是否丧失。[44]最后,如果将股东压制列为公司司法解散事由,可能会造成股东滥用司法解散之诉反向压制、敲诈大股东,这在英国法上是被禁止的。[45]
(二)增加与完善股权收购请求权
中国法官和他们的英美同行一样,对解散公司采取了谨慎和限制的立场。从第二部分英美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演变史中可以发现,在对公司僵局和股东压制的救济方式有限的情况下,法院以限制强制解散而拒绝救济属于一定历史阶段的必然结果,而后英美国家在公司司法解散救济之外,演化出灵活多样的衡平救济措施。我国可以借鉴英美法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发展多元化的救济措施,以替代司法解散的的单一救济。在英美的司法实践中,由一方股东收购另一方股东的股份,又是最为常见的救济方式。下文将具体从我国引入股权收购的可行性与具体制度设计展开论述。
1. 可行性分析:股权收购救济措施的本土实践
2008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二)》(简称《公司法司法解释(二)》)第5条尤其强调了法官在审理公司解散案件应当注重调解,鼓励各方达成妥协,通过股权收购、减资等方式解决股东矛盾,使公司存续。实践中也存在通过股权收购成功调解的案例。在张某诉某网络公司解散纠纷一案中,原告张某为公司小股东,与大股东矛盾尖锐,股东之间多次发生言语威胁和肢体冲突。为争夺公司控制权,还发生过暴力抢夺公章的行为,公司陷入僵局。法官在调解中了解到原告诉讼的真实目的并非解散公司,而是通过诉讼给大股东施加压力,维护自身利益。于是法官提出由大股东收购小股东的股权,并出于保护小股东的考虑,在调解中适当提高了收购价格。在历经九个月的审理和调解后,法院最终促成双方达成股权收购的调解协议。[46]我国法院股权收购的先例,说明股权收购作为司法解散替代性救济措施是具有本土可行性的。
与此同时,在2012—2021年间我国公司解散纠纷案件的调解结案率不到2.52%,[47]也就是说,在大部分的公司解散案件中,即便法院积极对股东进行调解,也很难促成股权收购。[48]股权收购调解的本质,是在司法的公信力下给小股东一次退出公司的谈判机会,但主动权仍在大股东手里。调解能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股东的态度是否强硬。由于封闭公司股权不存在公开的外部交易市场,少数股东很难在公司内部存在矛盾的情况下对外转让股权。大股东往往会利用这种对外转让的不可能性,压低收购价格。因此,这种不平等的谈判很难产生公平的结果。股权收购选择权相当于在司法介入下给予少数股东公平退出公司的机会,能够极大提高股权收购的成功率。
那么,在中国公司法中增加股权收购请求权会收获理想的司法效果吗?我们可以来观察美国实施法定买断权前后司法裁判的变化。Hetherington教授和Dooley教授曾对1960-1976年间判决的54个非自愿解散案件进行研究,其中只有3个案件涉及法院命令或法院监督下的买断,有16个案件被命令解散。在那些被拒绝救济和判决解散的案件中,54%的案件实际上以一方买断另一方而告终。[49]在1980年前后,美国一些州陆续颁布法规,允许股东行使法定买断权,购买原告的股份,从而终止司法解散程序。Haynsworth教授对1984-1985年间20个司法解散案件的研究发现,法院判决买断的案件比例与十年前法院判决买断加上股东协议买断之和的比例一致。[50]这种平行关系表明,增加法定买断权后的判决更准确地反映了当事人最终协商的结果,同时相比判决后的谈判成本更低,也具有经济合理性。
2. 具体设计:权利主体与公允价格
在股权收购请求权的具体设计中,最主要的两个问题是权利主体与公允价格的确定。本文认为,应当将股权收购请求权赋予原告股东。如果像《美国示范公司法》那样将股份买断权赋予公司或其他股东,会造成多数股东基于自己的控制地位拒绝购买,无法起到保护少数股东的应有功能。由原告股东主张股权收购请求权,法院决定由公司或其他股东购买其全部股份,给予少数股东退出公司的司法救济通道更为合理。
在公允价格的确定方面,可以首先由股东进行协商,如果无法达成一致,再由法院指定第三方评估机构评估确定。被收购的股份价格应当为公司的资产价值乘以相应的持股比例,少数股东的股权不因其小股东地位及封闭公司股份缺乏市场性而折价。[51]在类似于林方清案中存在隐藏在公司僵局中的压制行为,法官可以在判断公司构成僵局的基础上,辨认股东一方或双方可能存在的过错行为,在确定公允价格时应该充分考虑受压制的被收购者。[52]让难以合作的双方能够清白干净的分开是公司司法解散的制度价值,相比不对等的筹码式谈判,法院判决下的股权收购更加公平。[53]此外,由于收购者可能要承担一定的融资成本,法院可以允许分期付款以减轻收购者的现金流负担。[54]
当矛盾双方都想购买对方股东的股权,任何一方都不想退出公司时,决斗机制是一种理想的解决方式。一方面,一方报价另一方选择购买或出售股权的成本,要远低于双方协商和第三方机构评估的成本;另一方面,法官可以决定将报价权分配给具有信息优势的股东,最大程度降低由于信息不对称对弱势股东带来的,从而实现最优的结果。[55]虽然决斗机制是源于美国法的制度,但是在中国公司也有过类似的本土实践。万通六君子在早期的创业中就约定了以“决斗”来解决合作者之间的内部矛盾:当公司创始人合不到一起的时候,由一方出价把股份卖给别人,如果另一方不买就要以相同的价格出售自己的股份,最终留下的人出钱把走的人的股份买下来。这一僵局规则也帮助了万通在创业初期实现公司的持续地成长。[56]
(三)司法解散救济体系与股东压制救济体系的制度衔接
1. 股东压制中股权收购请求权的必要性分析
上一部分讨论了作为司法解散替代机制的股权收购请求权。而对于不构成公司僵局的股东压制,是否应该给予少数股东股权收购请求权呢?本文的观点是肯定的。[57]公司僵局是公司内部冲突对抗的极端状态,具体表现为在公司运营中无法获得必要的表决对关键性业务作出决定。但造成公司僵局的原因,既有技术层面,也有股东层面的。技术层面的原因包括相同的股权比例、偶数董事会、过高的表决权通过比例等,导致很容易在意见分歧时形成僵局。[58]这些技术层面的原因是可以通过股权结构的调整和公司治理结构的优化来避免的,但是造成公司僵局更深层的原因是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与矛盾,这些是无法靠技术来避免的。当少数股东因利益冲突而产生矛盾,股东关系不断恶化,人合性基础丧失,在控制股东对少数股东压制与排挤下,却因为不构成公司僵局,少数股东无法通过司法解散来退出公司,显然是不合理的。在最高院公报案例广西大地华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刘海公司解散纠纷案中,原告刘海是持有公司18.67%的小股东和公司董事,以公司已持续7年未召开股东会和董事会为由请求法院解散公司。在诉讼中,合计持股60.12%的三名大股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最高院认为,虽然公司长期未召开股东会,但是根据合计持股60.12%的股东明确表示不同意解散公司的事实可知,即便持股18.67%的股东刘海不参加股东会,华城公司仍可以召开股东会并形成有效决议,驳回原告解散公司的诉求。[59]公报案例为典型的大股东联手压制小股东,虽然不足以形成公司僵局,但是少数股东的权益受到了严重侵害,如果不给予少数股东退出公司的司法救济,少数股东只能在封闭公司持续受到压制,或者将股权低价转让给大股东,被挤出(squeeze out)公司。[60]因此,股东压制与公司僵局都应当成为股东收购请求权的事由。
对于已无意留在公司的股东而言,只能提起公司解散之诉,寻求退出公司。然而公司解散的正当性原则上只限于公司的功能或目的难以成就时,而非股东个人的去留。当股东只因想要退出公司就寻求司法解散,会对公司的名誉和其他股东的权益造成损害,亦非公司法之立法意旨。
2. 股东压制救济体系的规则构造
当前我国公司法对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压制的救济,分为孤立的单项权利救济和退出式的根本性救济,前者包括损害赔偿请求权、股东知情权、利润分配请求权,后者主要指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61]关于退出式救济,《公司法》第74条规定,(1)在公司连续五年盈利不向股东分红;(2)合并、分立、转让主要财产;(3)公司章程规定解散事由出现,股东会会议通过决议修改章程使公司存续的情况下,对股东会该项决议投反对票的股东可以请求公司按照合理的价格收购其股权。其中第(1)项规定的不分红属于典型的股东压制行为,但这一行为与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变更的性质完全不同。在美国公司法中,公司合并、分立等重大事项变更情形下的股权收买被称为异议股东评估权,规定在《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3章中;而公司僵局和股东压制语境下的股权购买属于股份收购权,规定在《美国示范公司法》第14章司法解散中。评估权的收买主体只能是公司自身,而股权收购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司,也可以是公司的其他股东。二者在行使程序和股权价格的确定方面都存在明显差别。[62]而现行公司法将这两种不同的制度规定在一个条文中,造成了法律逻辑的混淆。更为合适的做法是把《公司法》第74条中股东压制下的股权收购请求权分离出来,单独形成一个条文,与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分别进行规范。并对股东压制下的股权收购请求权的触发事由明确列举,具体包括不分配利润、无故解除公司管理职务和兜底条款等。
综上,我国公司法可以选择司法解散与股东压制的分别立法路径,并在《公司法》第十章第182条与第三章第74条分别增设或完善股权收购请求权作为救济方式,完善封闭公司股权收购的定价机制。
四、结语
封闭公司往往基于股东之间的相互信任而创立,正是因为相互信任,反而忽视了在经营过程中产生意见分歧和利益冲突的风险。就像不能保证所有的新婚夫妻不会离婚一样,也无法保证曾经共同打拼创业者不会分道扬镳。当公司在经营壮大的过程中出现公司僵局,如果股东之间没有事先约定僵局规则,公司僵局很难从内部打破。因此,法律提供的缺省规则就非常重要,能够在公司自我调节机制失灵时,从外部打破僵局。通过对英美法的公司司法解散制度的历史演变可以发现,对公司僵局的多元化救济是制度进化的方向与规律。当股东难以继续合作共同经营公司时,让一方退出是解决问题的最佳途径。我国法院股权收购的成功调解经验,说明股权收购作为司法解散替代性救济措施的可行性。本文认为,应在《公司法》第十章第182条针对公司僵局的司法解散与第三章第74条针对股东压制的救济制度中分别增设或完善股权收购请求权,能够为股提供东更低成本的退出机制,有效打破僵局,从而帮助有价值的公司持续成长。
(作者系清华大学法学院商法学博士研究生)
注释:
[1] 吴建斌:《公司纠纷指导案例的效力定位》,载《法学》2015年第6期,第56页。
[2] 学者对第8号指导案例的引用情况进行实证研究发现,法院判决解散正常经营公司的比例由此前的14%急剧提升至75%。参见张双根:载《指导案例制度的功能及其限度》,《清华法学》2017年第3期。
[3] 二人原为夫妻关系,在法院判决公司解散后离婚。参见吴建斌:《指导性案例裁判要点不能背离原案事实——对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67号的评论与展望》,载《政治与法律》2017年第10期,第123页。
[4] 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申请公司清算案,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苏中法商清预终字第00001号民事裁定书。
[5] 林方清与常熟市凯莱实业有限公司股东知情权纠纷,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8)苏0581民初2080号民事判决书,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5民终8851号民事判决书。
[6] 梁莎莎与戴小明房屋租赁合同纠纷,江苏省常熟市人民法院(2019)苏0581民初11384号民事判决书;梁莎莎与戴小明占有排除妨害纠纷,江苏省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20)苏05民终10824号民事判决书。
[7] 耿利航:《公司解散纠纷的司法实践和裁判规则改进》,载《中国法学》2016年第6期,第232页;张学文:《市场理性与法院自制——公司裁判解散的实证研究》,载《法学评论》2012年第1期,第37页;蒋大兴:《“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5卷第1辑,第45-46页。
[8] Margaret M. Blair, Locking in Capital: What Corporate Law Achieved for Business Organizer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51 UCLA Law Review 387, 392-294 (2003).
[9] 耿利航:《有限责任公司股东困境和司法解散制度——美国法的经验和对中国的启示》,载《政法论坛》2010年第5期,第135页。
[10]《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3版》,葛伟军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26页。
[11] Scottish Co-op Wholesale Society v. Meyer (1959) AC 324.
[12] F Hodge O'Neal, Robert B Thompson, O’Neal and Thompson’s Oppression of Minority Shareholders and LLC Members, Rev. 2nd ed (2004)
[13] Paul L. Davies, Sarah Worthington, Gower: Principles of Modern Company Law. 10th ed. London: Sweet & Maxwell, 2016, p.977.
[14]《英国破产法》,丁昌业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15] 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MBCA) Chapter 14 Dissolution, Subchapter C. Judicial Dissolution
[16] Harry J. Haynsworth, The Effectiveness of Involuntary Dissolution Suits as a Remedy for Close Corporation Dissension, 35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25, 89-90 (1987).
[17] [美]汉密尔顿著:《美国公司法:第5版》,齐东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7页。
[18] 《英国公司法》没有明确规定不公平损害的含义,英国学者对其表现形式作出了列举式的归纳,主要包括:被排挤出管理层、不提供信息、不正当地操纵持股、修改公司章程、违反董事义务、过高的薪酬、不分红、管理不善、程序不当等。参见:《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3版)》,葛伟军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27-828页。
[19] 《英国2006年公司法:第3版》,葛伟军译,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829页。
[20] 《美国示范公司法》在第十四章专章规定了解散(dissolution),分别包括公司的自愿解散、行政解散和司法解散。
[21] 详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 14.30(a) (2)条。
[22] 该节的其他条款还规定了由司法部长(attorney general)以及债权人提起司法解散的事由。
[23] 《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 14.30条官方评论。
[24] Douglas K. Moll, Reasonable Expectations V. Implied-In-Fact Contracts: Is the Shareholder Oppression Doctrine Needed?, 42 Boston College Law Review 989 (2001)
[25] 《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4.30(b)条。
[26] 《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4.34条。
[27] Harry J. Haynsworth, The Effectiveness of Involuntary Dissolution Suits as a Remedy for Close Corporation Dissension, 35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25 (1987).
[28] 普通救济的范围非常广泛,包括修改公司章程、撤销董事或其他高管的职务、任命董事或高管、任命代管人、任命临时董事、作出分红、对受害方的损害赔偿等。
[29] Model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 to MBCA, Section 40-43.
[30] John H. Matheson and R. Kevin Maler, A Simple Statutory Solution to Minority Oppression in the Closely-Held Business, 91 Minnesota Law Review 657 (2007) .
[31] J. A. C. Hetherington & Michael P. Dooley, 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 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 63 Virginia Law Review 70-75 (1977).
[32] [英]A.J.博伊尔著:《少数派股东救济措施》,段威、李扬、叶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43页。
[33] 1984年《英国公司法》第461条。
[34] 1986年《英国破产法》第122条。
[35] U.K. Law Commercial Report No.246 (1997).
[36] [美]汉密尔顿著:《美国公司法(第5版)》,齐东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8页。
[37] 又被称为猎枪机制(shotgun mechanism)、收购或出售条款(buy-sell provisions),俄罗斯轮盘赌(Russian Roulette)。本文认为决斗机制这一译名更能够体现这一规则所蕴含的西方文化特:这一冒险的僵局解决规则,就如中世纪的骑士们以开枪决斗来决一胜负一样。关于shootout mechanism的其他中文译名参见:[德]霍尔格·弗莱舍尔、斯特凡·施奈德著《合伙与封闭公司中的点杀出局条款——法律比较与经济理论的进路》,王萍译,载《财经法学》2016年第6期,第104-105页。
[38] 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Model Real Estate Development Operating Agreement with Commentary, 63 Business Lawyer 472 (2008).
[39] Louis T. M. Conti, Lisa R. Jacobs and Steven N. Leitess, Deadlock-Breaking Mechanisms in LLCs—Flipping a Coin Is Not Good Enough, but Is Better Than Dissolution, Business Law Today (March 2017), pp. 1-6; Claudia M. Landeo and Kathryn E. Spier, Irreconcilable Differences: Judicial Resolution of Business Deadlock, 81 University of Chicago Law Review 203 (2014) .
[40] Claudia M. Landeo & Kathryn E. Spier, Shotguns and Deadlocks, 31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146 (2014).
[41] Valinote v. Ballis, United State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Seventh Circuit 295 F.3d 666 (2002)
[42] 李建伟:《司法解散公司事由的实证研究》,载《法学研究》2017年第4期,第117页。
[43] 14个州没有将股东压迫作为解散的法定情形,参见J. A. C. Hetherington & Michael P. Dooley, 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 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 63 Virginia Law Review 70-75 (1977).
[44] 黄辉:《现代公司法比较研究:国际经验及对中国的启示》,清华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284页。
[45] [英]A.J.博伊尔著:《少数派股东救济措施》,段威、李扬、叶林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版,第145页。
[46] 沈志先主编:《诉讼调解》,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第285-287页。转引自俞智源:《公司僵局的预防与破解》,载法律出版社2014年版,第123页。
[47] 笔者在聚法案例网(https://www.jufaanli.com/)以公司解散纠纷为案由进行检索,检索结果显示2012-2021年公司解散案件共有15908件,其中调解结案的案件有400件,占比2.52%。
[48] 在林方清案中,双方股东都想要购买对方的股权,但都被对方拒绝。法院与服装城管理委员会进行了多轮调解,但始终未能就收购方和收购价格达成一致。
[49] J. A. C. Hetherington & Michael P. Dooley, Illiquidity and Exploitation: A Proposed Statutory Solution to the Remaining Close Corporation Problem, 63 Virginia Law Review 70-75 (1977).
[50] Harry J. Haynsworth, The Effectiveness of Involuntary Dissolution Suits as a Remedy for Close Corporation Dissension, 35 Cleveland State Law Review 25 (1987).
[51] 《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3.01条。
[52]《新泽西公司法》就着重强调了公允价格与账本价格的偏离,授权法院确定“在诉讼开始之日或法院认为公平的较早或较晚日期,加上或减去法院认为公平的任何调整”的价值。参见New Jersey Revised Statutes §14A:12-7(8)(a)
[53] 林少伟:《英国现代公司法》,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80页。
[54] 《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4.34条。
[55] Claudia M. Landeo & Kathryn E. Spier, Shotguns and Deadlocks, 31 Yale Journal on Regulation 183, 184 (2014).
[56] 冯仑:《扛住就是本事》,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0年版,第17-20页。遗憾的是,笔者查阅万通公司的章程,没有找到这一规则,或与冯仑退出万通另外创业有关。
[57] 相同观点参见蒋大兴:《“好公司”为什么要判决解散——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8号评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5卷第1辑。
[58] [美]汉密尔顿著:《美国公司法:第5版》,齐东祥等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270页。
[59]最高人民法院(2017)最高法民再373号民事判决书。
[60] 彭冰:《理解有限公司中的股东压迫问题——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案例10号评析》,载《北大法律评论》2014年第15卷第1辑。
[61] 本文中的异议股东回购请求权与股权收购请求权为两种不同性质的权利,前者是指股东反对公司重大行动(如合并、分立)时,有权要求公司回购其股份,规定在《公司法》有限责任公司第74条第(2)项和第(3)项、股份有限公司第142条第(4)项;后者是指在公司僵局与股东压制中,股东请求其他股东或公司买断其股份的权利,规定在《公司法》第74条第(一)项。
[62] 张学文:《有限责任公司股权收买请求权的制度评价与立法完善》,载《海峡法学》2010年12月第4期。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沙龙分享群。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点击下方链接保存课件。
点击下载金融科技大讲堂课件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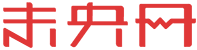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