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分享
本文共字,预计阅读时间。
摘要:珠峰公司案、绿洲公司案、申华公司案、恒通公司案的判词呈示出公司权力配置的两大迷思。而该两大迷思无法通过司法层面上的逻辑推演来化解,回归公司权力配置的基点,完善立法方为迷思纾解之道。在对政治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应用极端化的批判中确立了公司权力配置的两大基点,即效率目标与协商基础。以效率目标与协商基础为基,以对中国法、美国法、德国法的比较法研究为法,对标准公司与封闭公司权力配置的边界与形式进行了分别讨论,最终重构了公司权力配置的图景。
关键词:公司权力配置 股东会 董事会 效率目标 协商基础
一、司法判词之下的公司权力配置迷思
公司权力配置乃公司法学之基本问题,亦是本轮公司法修改不容忽视的重大问题。自我国《公司法》问世已来,虽已历五次修改、五部解释,但对此问题却仍无令人满意之回应,此不得不谓为《公司法》之缺憾。而此等立法缺憾则造成了法律实践当中的迷思,此于相关司法判词中颇为显彰。[1]
(一)珠峰公司案[2]
珠峰公司案历经一审、二审直至2017年最高人民法院再审,其争议焦点之一乃是“珠峰公司之《公司章程》的二十七条有无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据其《公司章程》第二十七条,珠峰公司自主对公司资产开发,由董事会决定并向股东大会报告即可,原告认为此违反了《公司法》三十七条的规定,即“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属于股东会之法定职权,其不应由董事会行使。
对之,二审判词如是阐论:“公司章程是调整公司内部组织关系和公司经营行为的自治规范,体现的是公司全体股东的共同意思。从珠峰商贸公司《章程》关于股东会职权范围的上述规定来看,其并未剥夺我国公司法赋予股东会行使的‘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等相关重要职权;且我国公司法亦允许公司章程对股东会职权进行其他规定。”[3]
而最高院则于其再审判词中对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条款的性质作了进一步的明确,即“《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四十六条分别是有关股东会和董事会职权的相关规定,并不属于效力性强制性规定。而且根据《公司法》第四条规定,公司股东依法享有选择管理者的权利,相应地该管理者的权限也可以由公司股东会自由决定,《公司法》并未禁止有限责任公司股东会自主地将一部分决定公司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的权力赋予董事会。”[4]
据此,股东会职权与董事会职权似乎可自由配置,而且根据最高院的判词,公司权力配置方式似不局限于公司章程形式。此等观点在最高院法官虞政平博士所著之《公司法案例教学》(第二版)所选取的相关经典案例(以下简称“虞书案”)判词中亦有体现,即甲集团股东通过充分商讨,将属于股东会投资决策权中的部分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并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不应予以限制或禁止。股东会职权的行使主体并不具法定排他性,该集团公司股东会限缩自身的部分职权而将其授权董事会行使,不违背股东会职权的性质。[5]然此等结论是否足以让人信服?公司所有权力是否皆可自由配置?比如修改公司章程决议权与解散公司决议权能否授予董事会行使?于此不无疑虑,仍需探讨。
(二)绿洲公司案[6]
绿洲公司案二审判词似乎可以修正上述结论并给了我们一个完整的总结,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三十八条、第四十七条分别以列举的形式规定了股东会和董事会的职权,从两条法律规定来看,董事会、股东会均有法定职权和章程规定职权两类。无论是法定职权还是章程规定职权,强调的都是权利,在没有法律明确禁止的情况下,权利可以行使、可以放弃,也可以委托他人行使。
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从此条规定中的法律表述用语‘必须’可以看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的决议有且只有公司股东会才有决定权,这是股东会的法定权利。”[7]
暂不究诘此判词中的某些细节问题,如,职权是否等同于权利?是否可以放弃?该判词似乎描绘了一个这样的权力配置图景:除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决议属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外,其它公司权力皆可自由配置。于此,笔者需再追问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公司决议属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规定是否合理?其法理依据为何?而除此之外的其他公司权力是否皆可自由配置?如《公司法》赋予股东会选举非职工董事的权力可否授予董事会自己行使?
(三)申华公司案[8]
在申华公司案中,申华公司《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规定:“股东大会闭会期间,董事人选有必要变动时,由董事会决定,但所增补的董事人数不得超过董事总数的三分之一。”而该规定是否违反《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乃本案之争议焦点。对此,二审法院认为:我国《公司法》明确规定了股份公司股东大会、董事会的性质与职权,股东大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选举和更换董事的职权由股东大会行使;董事会对股东大会负责,执行股东大会的决议,为公司的执行和经营决策机构,因此《公司章程》第十八条违反了《公司法》,该规定不具有法律效力,而申华公司董事会所作出的相关决议超越了我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的权限,违反法律,侵害了股东的权益。[9]
值得注意的是,申花公司案所适用的法律是1993年《公司法》,而1993年《公司法》所规定的股东会职权与董事会职权条款中均无2005年《公司法》相应条款中“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这样的表述,此是否可成为与珠峰公司案、绿洲公司案、甚至虞书案判词不同之缘由?然事实上,虞书案发生于2004年,其所适用的法律依然为1993年《公司法》,如此,法律的修改似乎不是判词差异的真正缘由。于此,我们再作进一步假设和追问:若申花公司案发生于今日,其《公司章程》将选举董事之权配置于董事会可被接受?那么,选举监事之权是否也可配置于董事会呢?因此,绿洲公司案二审判词所描绘出的公司权力配置图景似乎仍有极大探讨空间。
(四)恒通公司案[10]
在珠峰公司案中,最高院的再审判词所含之观点“公司权力配置方式不局限于公司章程形式”在恒通公司案的二审判词中得以明确阐论,概言之,恒通公司股东会以普通决议的方式将原本属于股东会的职权授权给董事会,此已构成对《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根据《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的规定,股东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但恒通公司股东会通过该决议的比例并未达到这一法定比例。因此,股东会决议的内容违反了《公司法》的规定,应认定为无效。[11]
据此判词,股东会似可以公司章程以外之形式配置公司权力,但若涉及《公司章程》的实质性修改,需履行与修改章程一样的程序,方符合《公司法》之强制性规定。此观点有无值得商榷之处?同时,基于此观点,可否向前再进一步,股东会在不以公司章程或特别决议进行权力配置的前提下,能否以特别决议方式径行法律或章程赋予董事会之权力之决议呢?如股东会以特别决议方式直接聘任或解聘经理?
(五)公司权力配置的两大疑问
以上四案判词之下的公司权力配置迷思可归结为两大疑问:
第一,公司权力配置的边界问题,即股东会和董事会的权力边界为何?哪些公司权力不允许依股东意思而作另外配置?
第二,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问题,即可否以公司章程以外的形式配置公司权力?股东会可否以特别决议方式径行董事会权力?
此两问当如何纾解?其属司法纰缪,还是立法疏漏?此需作进一步检视。
二、从司法到立法的学术检视
纵观前述四案,虽判词有疑,但其内在逻辑统一,具体而言,公司权力配置的边界问题应考量公司章程于公司法之优先性,即公司章程所作之权力配置在不违背强制性规定的前提下,优先于公司法所作之权力配置;同时,股东决议等公司章程以外的形式与公司章程本质上并无二致,其皆为股东团体意思之载体,故二者不会因形式之别而有异。观此逻辑,法院用以解决公司权力配置之疑者,非为公司法,而是作为私法一般法的民法,具言之,乃是无论公司章程,还是股东决议等其它形式俱属贯彻股东团体意思之法律行为,而法律行为当然优先于公司法的非强制性规定;但若继续推演,公司权力配置问题依然陷于无解,即公司法所作之权力配置是否属强制性规定,或其中哪些权力配置属强制性规定未有定论,同时,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未于公司法层面上作特别考量似有不周,究其原因,此皆因作为特别法的公司法规定存有疏漏而致司法逻辑闭环之未成。
观《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与四十六条之规定表述,[12]立法者并未明确将之列属强制性规定范畴,如此,“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中的“职权”似不应作为股东会或董事会独占之权,尤值注意的是,该条文以“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作兜底条款,公司权力可自由配置似符合立法意旨;然2018年证监会新修订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对此则表现出不同观点,其第十四条规定:“上市公司应当在公司章程中规定股东大会对董事会的授权原则,授权内容应当明确具体。股东大会不得将法定由股东大会行使的职权授予董事会行使。”于此语境下,公司章程另作配置的“其他职权”则应被解释为“法定职权”之外的“其他职权”。[13]对此两种观点,学界皆有不同论说支持,[14]然随着讨论深入,兼采两种论说的折衷观点逐渐为大多数学者所认同,如赵旭东教授即认为公司法中的权力配置条款的属性不应一概而论,股东会、董事会的各个职权应根据是否具备专属性质来确定其是否可另作配置,因为具备专属性的职权让渡势必会造成使公司机关形骸化。[15]折衷观点虽直摄公司权力配置之底层法理,然从立法语言上,却实难以此意推解,立法疏漏由此可见一斑。
再观《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与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之规定表述,[16]其属强制性规定,“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被认定为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似乎无疑。然此并不能反推该条款所列职权以外者皆为非不可让渡之权,因为根据上下文意,该条款强调的是所列职权应适用股东会特别表决程序,而非对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范围的划定;同时,就该条款所列职权,其不可让渡性是否皆具充分之法理支撑,笔者亦不无疑虑。
复观《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与四十六条之兜底条款,其仅指明公司章程乃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之一,而并未禁止以公司章程之外的形式配置公司权力,故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似不局限于公司章程。此观点是否周延?笔者认为尚需置于公司法学语境中加以考量,探究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股东决议于公司权力配置而言是否存在差别。纵观学界对公司章程性质的讨论,较有影响者无外乎四种论说,即合同说、决议说、自治法说,以及折衷说,[17]其中,前两种论说认为公司章程与股东协议、股东决议性质相通,据此,三者所作之公司权力配置似无甚差别。对此,笔者存有不同意见,暂不论三者于一般意义上的差异,单就不同公司之权力配置而言,公司章程所体现的性质并不相同,非可一褱而论。以对股东人数众多、股权极度分散公司的权力配置为例,公司章程则更多强调公司之团体性,其作为自治法的性质即更加突出,故兼取而折衷的章程性质论说更具有说服力。如此,股东决议、股东协议等形式与公司章程并不能完全等同,就其间差异讨论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仍具有重要意义。
据上所析,公司权力配置的两大疑问无法通过司法层面上的逻辑推演来化解;着眼于立法上的疏漏,完善《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方为迷思纾解之道。对此,仅于法学视阈下讨论公司权力配置的立法修正问题可能难以获得令人满意的答案,故多数学者并未沿循此研究思路,而是希冀通过政治学理论或经济学理论来讨论并构造公司权力配置的应然图景;然此等讨论难免又会陷于理论极端化应用之情及相应的学术纷争,而忽视对公司权力配置方法论的挖掘。因此,笔者认为,若欲重构公司权力配置的立法图景,则需先拨开迷雾,找寻公司权力配置的基点,以道御术,方可至成。
三、回归公司权力配置基点:从理论应用极端化批判到两大配置基点确立
纵观我国《公司法》的立法史,目前我国公司权力的配置样态可能更多地出自于立法者对旧有路径之依赖,即对国家权力配置的取法,而非为对商业实践总结而成之“中国特色”。[18]如此,在解释上亦更多地表现为对政治学理论的关注。然此等解释论及其基础上所构之权力配置样态已在实践中产生了诸多问题,政治学解释似显捉襟见肘。[19]因此,我国学者亦多有在经济学层面上寻求解释的努力。在方法论层面上,无论是政治学理论,还是经济学理论都为公司法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视阈。但是,任何理论皆不可被极端化应用,更不可不加批判、修正地奉为至上不变之圭臬,因为理论的极端化应用不仅不会帮助我们纾解公司权力配置问题,反而会引致重重迷雾,掩盖问题所指向的本质。因此,面对此等理论应用极端化之情,我们应先破后立,在批判中回归公司权力配置基点。
(一)政治学理论应用极端化之批判
很长时间以来,以国家权力配置解释公司权力配置被视为毋庸置疑之法,此情于我国尤为突出。究其原因,可能有二:
其一,公司列属“法人”之范畴,即公司乃法律之产物,故公司即应依法定条件和程序设立。[20]此等法定条件和程序于早期主要体现为公司设立须取得国家的“特许令状”(charter),当时的法律十分强调国家在公司设立当中的作用,如此公司即常被视为国家权力的延伸,[21]其奉行与国家类同之权力配置安排似谓合理。我国《公司法》的问世和发展与国有企业改革密不可分,故上述观点极易被接受,然随着时代发展,我们现早已抛弃此等“特许权理论”,公司设立已由“特许主义”、“核准主义”演变至今时之“准则主义”,国家在公司设立中的作用亦由“创设作用”转变为“确认作用”,如此,公司权力配置类同国家权力配置之观点的正当性基础已然动摇,故如今“理所当然”地坚持此等观点很大程度上乃是对旧有路径之依赖。
其二,我国《公司法》制定初期,对公司权力配置理论关注不够、研究不足,如此,即以“默认知识”填补漏缺,将政治制度简单地翻版于《公司法》当中乃属当时立法者之自然行动,[22]此于立法者所使用的某些用语中即有体现。例如,《公司法》第三十六条中有“股东会是公司的权力机构”的表述,此乃《宪法》对人民代表大会之表述;又如《公司法》第四十六条中有“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的表述,此明显将董事会比照行政机关而定位。
观此二点,于今时,我们是否还能毫无怀疑地认定国家权力配置与公司权力配置的天然相通性?是否还能理所当然地将国家制度与公司制度相互比照而自由移植?笔者对此颇感疑虑。当然,笔者并非在彻底否定以政治学理论探讨公司权力配置问题的意义,事实上,斯蒂芬.博顿利教授(Stephen Bottomley)、施天涛教授、邓峰教授等学者的研究十分有益,颇值关注。[23]笔者所反对的是将政治学理论进行极端化的应用,即将作为方法论的政治学理论异化为作为本体论的政治学理论,简言之,将公司视同与国家性质相同的组织实体来进行权力配置考量。此等极端化的理论应用甚至于法律实践中亦有表现,例如在华城地产集团有限公司与宁波开元华城置业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撤销纠纷案(以下简称“开元华城公司案”)的二审审判中原告即曾申张如此理据:“一审判决在认定股东会审议权限时,忽略了公司权力分配的基本制度以及《公司法》‘三权分立与制衡’的核心价值。”[24]
事实上,当我们回观洛克、孟德斯鸠等先贤的观点时,我们即应知道国家权力配置的目标乃是制约公权、保障私权;然公司权力配置的目标则并非如此,公司是一个效率组织,其为效率而生,因此,公司进行权力配置的目标即应着眼于效率,即通过高效地整合资本、才智等各种资源,促进公司收益的提升,成本的减少。于此,开元华城公司案中所谓“三权分立与制衡”乃至所有权力制约措施皆可作为公司权力配置的方法而非权力配置本身,其可成为在效率目标下进行公司权力配置的结果而非依据,换言之,若“三权分立与制衡”等权力制约措施无法实现公司运营的效率目标,则应进行进一步之优化、改进,甚至扬弃。
(二)经济学理论应用极端化之批判
自美国经济学家罗纳德.科斯(Ronald Coase)所撰文章《企业的性质》(The Nature of the Firm)于1937年发表后,对公司问题进行经济解释即兴荣未艾,后经阿尔钦(Alchain)、德姆塞茨(Demsetz)、詹森(Jessen)、麦考林(Meckling)、威廉姆森(Williamson)、麦克尼尔(MacNeil)、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费希尔(Fischel)等学者的不断探究,公司合同理论正式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根据此理论,公司被视为一系列合同之联结(nexus of contracts),此等合同联结使得股东、管理者、劳动者、债权人、消费者等众多要素提供者相联;[25]而以此为基所形成的“交易费用理论”[26]和“委托代理理论”[27]即成为了解释公司法问题之重要工具,即基于此论,包括公司权力配置在内的所有的公司制度安排均应致力于减少交易费用和控制代理成本。此不仅对经济学影响深远,更给公司法学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思维维度。
然正如前文所论,任何理论皆不可被极端化应用,经济学亦不例外。但遗憾的是,亦有学者将公司合同理论推演至极端化,其具体表现有二:
其一,公司合同理论有一个重要的观点,即公司是联结股东、管理者、劳动者、债权人等众多要素提供者的合同联结;据此推演,股东作为资本要素提供者,似不应比其他要素提供者地位高,因此,股东似乎不应被当作公司之所有人,如此,公司之目的不应为股东利益最大化,而应着眼于股东、管理者、劳动者、债权人、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之利益,乃至社会利益,此可谓为“公司利益相关者理论”或“公司社会责任理论”。[28]
其二,既然公司是一系列合同之联结,那么,股东即可以其自由意思通过合同来安排包括公司权力配置在内所有公司制度。如此,为何还需制定公司法?公司法存在的意义又是什么?对此,伊斯特布鲁克(Easterbrook)作出修矫式的回应:“公司法是一套现成的法律条款,它可以节省公司参与者签订合同时所要花费的成本。”[29]也就是说,基于交易成本的考量,公司法有其存在的意义,其为股东提供了公司合同的示范文本。如此,紧接而来的推论即是:公司法既然是示范文本,那么,就应当是否允许股东通过协商自由变更公司法条款,包括对被公司法所确认的公司权力分布形态进行改变。
对上述两论,笔者回应如下:
第一,就公司社会责任理论而言,事实上,其理论基础并不局限在公司合同理论,其支持者所引论据角度多元。多德教授(E. Merrick Dodd)是公司社会责任理论的代表,其甚至在1927年至1932年间与坚持股东利益至上的伯利教授(Adolf. A. Berle)展开了激烈的论战;[30]但颇具戏剧性的是,两位学者最终都修改了自己的原有观点,向对方观点进行转变。[31]这从论战到转变的过程充分说明股东利益至上论与公司社会责任论各有其长。
然就公司目的而言,公司首先应致力于股东利益最大化,当我们细察公司利益相关者时,即不难发现无论是管理者、劳动者,还是债权人、消费者皆有相应的对价与风险补偿机制,而唯独股东居于公司剩余收益索取者和经营风险最后承担者之地位,[32]因此,公司以股东利益最大化为其根本目的具有正当性。事实上,在世界范围内,公司治理有进化趋同之势,“股东导向模式”(Shareholder Oriented Model)已成主导模式。[33]此于我国立法层面上亦非常明确,即根据《民法典》第七十六条规定,公司属营利性法人,而营利性则是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为目的。
至于社会责任,其绝不可改变公司营利法人的属性。事实上,公司的社会责任应通过合同、公共政策来落实,而非将社会责任引入公司治理之中。[34]
第二,公司法有其作为公司合同示范文本的作用,但并非所有公司法条款皆为示范文本。公司法的强制性除了源于公共政策要求外,还源于公司运营的效率目标,即通过协商进行公司权力配置只是手段,而以此促进公司运营的效率性才是最终目标。
那么,协商一定能带来效率吗?此并不一定,但充分协商之下的权力配置安排可以被视为股东为实现效率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具有正当性。但是,当股东人数众多,甚至股权极度分散,即会有相当部分的股东对参与公司经营的态度冷漠,此等协商则并不充分,若此等不充分协商下的相应权力配置安排不能确保客观上公司运营的效率性,则这样的权力配置安排无法获得正当性基础。而事实上,在股东人数众多、股权分散的公司中,股东从事商业判断和经营的能力往往参差不齐,单纯进行众意集合极难促进公司运营的效率目标,此或限于集体决策的困境,或限于巨大的代理成本之中。如此,面对此等协商基础较差之情形,基于效率目标而设置的公司法强制性条款具有重大意义。[35]
(三)两大配置基点之确立:效率目标与协商基础
通过对政治学理论与经济学理论应用极端化的批判,我们不难发现公司权力配置的基点。在对政治学理论应用极端化的批判中,我们正是基于对公司效率性的把握,才界分了公司权力配置与国家权力配置在目标上的不同。而在对经济学理论应用极端化的批判中,我们又进一步明确了公司权力配置的效率目标,具体而言,公司的营利性属性是对公司权力配置安排效率目标的进一步诠释;而公司合同理论则为我们促进公司权力配置的效率性提供了重要工具,于此注意,公司合同理论仍然是方法论层面上的,此正如罗培新教授所言:“公司合同理论,与其说是解释了公司的本质,还不如认为它提供了一种解释公司的方法。”[36]如此,深究其道,无论是科斯(Coase)对公司合理理论奠基性的精彩阐论,还是随后发展而来的交易费用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其皆是对公司制度安排效率性的追问,故避免公司合同理论应用极端化,回归效率目标,公司权力配置方能趋近最优,而于此,对股东协商基础的审视是我们不容忽视的关键。如此,公司权力配置的基点即已找出,即效率目标与协商基础。
四、重构公司权力配置图景:两种公司形式中权力配置的边界与形式
据上文所论,公司权力配置的迷思可归结于公司权力配置边界与形式两大问题。对于这两大问题的回应须于不同的公司形式中作具体探讨,如此,方可得全面之公司权力配置图景。
论至公司形式,需回向于公司的功能。公司作为商业经营形式无外乎有两大功能,即聚合资源与限制责任。以上市公司等股东人数众多,甚至股权分散的公司为例,公司的功能不仅仅是为股东划定了投资风险隔离墙,更是为资本、人力资源的聚合提供了可靠的机制,即众多投资者聚合于股东会参与公司治理,而管理人才则聚合于董事会及董事会之下的管理层直接管理公司,如此,在此等全体股东将管理权让渡于管理者,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公司经营形态之下,公司的两大功能得以完整显现,因此,笔者名之为“标准公司”。然亦有经营者非出于聚合资源考虑而选择公司形式之情,此类公司股东人数较少,彼此之间往往亦有相互信赖之关系,公司股东希望直接管理公司,而非欲将管理权进一步让渡,其选择公司作为经营形式仅出于限制责任之考虑,对于此类公司,笔者名之“封闭公司”。[37]
值得注意的是,自进入二十一世纪,世界各国公司法在竞争中大有趋同融合之势。[38]因此,对于各国公司法改进的重要蓝本《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odel Business Corporation Act, MBCA)[39]、《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aware General Corporation Law, Del. GCL)[40]、《美国封闭公司示范补充规定》(Model Statutory Close Corporation Supplement, MSCCS),以及大陆法系公司法的重要代表《德国股份法》(Aktiengesetz, AktG)[41]、《德国改组法》(Umwandlungsgesetz, UmwG)[42]、《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Gesetz betreffend die Gesellschaften mit beschränkter Haftung,GmbHG)[43],我们应予重视。故笔者拟立足我国《公司法》,以比较法研究为法,重构我国公司权力配置的图景。
(一)公司权力配置的边界
1. 标准公司的权力配置边界。在标准公司中,公司的经营呈现出所有权与管理权相分离的形态,导致如此形态产生的原因是众多而分散的股权分布无法使得管理权保留于股东会层面,即股东间的协商基础较差,集体决策的困境以及参差的管理能力会使得公司偏离其效率目标。因此,基于对标准公司效率目标与协商基础的考量,全体股东即将管理权让渡于管理人才,而这些管理人才或来源于股东群体内部,或源于职业经理人市场中,他们组成了标准公司的董事会,正如罗培新教授所论,即董事相较于股东更长于经营,将管理权赋予董事会会降低公司的经营成本。[44]如此,标准公司的权力配置应首先应确保董事会的经营中心的地位,事实上,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还是主要的大陆法系国家,此观点其已被普遍接受,[45]然我国《公司法》在此关键问题却不明确,此是引致公司权力配置迷局重要原因;同时,基于对董事会代理成本的控制,标准公司的权力配置还应致力于确保股东会拥有控制代理成本之充分权力。[46]因此,标准公司的权力配置应围绕着董事会经营权与股东会控制权两个维度展开。
由于公司经营权所涉及之广泛,公司法无法穷尽列举或精准描述,故对于董事会的权力,公司法宜作反向推演,即以“董事会权力=公司所有权力—股东会权力—监事会权力”作为权力表述公式。据此,公司法可作如此规定:“公司所有权力皆归董事会或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除非本法和X另有规定。”此等法律条款的表述于相关立法例中亦可找到支持,如《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的第8.01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的第141条第(a)款,以及《德国股份法》(AktG)第76条第(1)款皆有类似表述;而且为了确保董事会的经营中心的地位,《德国股份法》(AktG)的第119条第(2)款甚至还规定:“股东大会只能在董事会请求时对公司经营的问题作出决定。”
而上述法律条款表述中的“本法另有规定”则既包括配置于股东会之权,亦包括配置于监事会之权,但受题旨所限,本文即略去配置于监事会之权,而只探讨配置于股东会之权;至于“X”,此乃公司权力配置的自治手段,即可通过“X”将公司法配置于股东会或董事会的权力进行再配置,其具体指什么?是章程?抑或是股东决议、股东协议等公司章程以外的其它形式?这是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问题,我们于下一个小节再作探讨。如此,公司权力配置边界问题的解决有赖于对“哪些权力应属配置于股东会的权力,且不允许‘X’进行再配置”问题的回应,即公司法必须对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予以明定。当然,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回答“董事会经营权是否可通过‘X’配置于股东会”的问题,如此,公司权力配置边界方能得以清晰划定。
先论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哪些权力应属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如前文论,标准公司的权力配置应确保股东会拥有控制代理成本之充分权力,如此,对代理成本的控制即是判断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标准。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这些权力是否皆应归属于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除了这些权力外,是否还有其它权力亦需加以考量?如,董事和监事选举权、分红决议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笔者认为于斯殊值探讨。详论如下:
(1)对公司章程修改权之考量。公司章程修改权归于股东会似无需详论,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之最高效力文件,是股东团体意思之最重要载体,公司章程修改权归于股东会具有法律逻辑上的自恰性。而单从公司权力配置角度论,公司章程涉及公司权力配置之根本,将其修改权配置于股东会对于董事会以及董事会领导下管理层的代理成本控制具有不容忽视的重要意义,具言之,于标准公司之中,股东会可根据自身实况通过章程自治来实现对董事会及管理层违信等不当行为的防范与规制,以确保公司运行不偏离其经营目标。[47]因此,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将公司章程修改权列属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亦具有公司权力配置上的正当性。
以比较法的视角观,《德国股份法》(AktG)与我国《公司法》持相同观点,[48]但《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与《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的规定似存有差异,即在二者中,公司章程修改权在一定程度上亦被董事会所分享。[49]对此,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公司合同理论在美国法中的贯彻,即公司章程乃是所有者与管理者之合同,因此,公司章程的修改亦应考虑董事团体的意思;但这种解释并不能令人信服,暂不论公司章程是否可与合同等同而视,美国法中公司章程修改权配置也并非围绕所有者与管理者平等合意的理念来设计,即公司章程最终修改权仍由股东会所保留。[50]因此,与其陷入公司合同解释论说的泥潭,不如从标准公司权力配置的两大维度观之,即公司章程中无可避免地会涉及公司经营事项,董事会基于其经营中心的地位而享有一定公司章程修改权,但与之相伴的是董事会成员及关联人员篡夺股东权益道德风险的增加,故股东会通过保有公司章程最终修改权来控制代理成本极有必要。如此,美国法虽赋予了董事会更多的权力,但股东会依然是公司章程的最终决定者,此中法理与我国《公司法》、《德国股份法》(AktG)所持观点仍具有一致性。
(2)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之考量。公司合并、分立、解散与变更形式属于公司重大变更,此关乎公司根基,即公司是否存在以及以何形式存在,因此,于作为公司剩余收益索取者和经营风险最后承担者的股东而言,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公司章程修改权。[51]如此,若将此权配置于董事会,其间则会产生巨大代理成本,具体而言,董事会的一招不当行权即会造成股东难以承受之损失,即重大变更后的公司复归原形之成本巨大;同时,公司的重大变更对于董事而言无异于中期选举或信心重估,故股东会可通过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选举”或“罢免”董事,此乃是代理成本控制的不容忽视之法。[52]因此,无论从消极地防范代理成本角度,还是积极地控制代理成本角度言,公司合并、分立、解散与变更形式决议权作为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不应有疑。此等观点不仅于我国《公司法》、《德国改组法》(UmwG)、《德国股份法》(AktG)中得以确认,[53]在《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中亦有体现。[54]
(3)对增资、减资决议权之考量。公司资本关涉股东权责、公司财源,以及债权人保护三大方面。[55]其中,对债权人的保护,各国公司法通过专门的保护条款来实现,其无涉增资、减资决议权配置之讨论,因此,就本文论旨,我们应从股东权责与公司财源两大维度进行考量。
于股东权责维度而言,增资或致股东有限责任范围扩大,或致股权稀释,或兼而有之,无论是何结果,此皆关乎股东之切身利益,因此,为防止由此而生之代理成本,此权配置于股东会较为合理。至于减资,其非但不会扩大股东有限责任,反而会缩减股东有限责任;同时,其也不会导致未与公司达成股权回购合意的股东的股权稀释问题,如此,减资决议权似无须保留于股东会。
于公司财源维度而言,公司资本列属公司运营的重要财源,其增加或减少乃属公司经营判断的范畴,尤其是随着公司实践与资本市场的发展,公司通过资本增减进行市值管理、股权激励、资本结构调整等已成为了公司经营之新常态,因此,基于对标准公司效率目标与协商基础的考量,增资、减资决议权似又应配置于作为公司经营中心的董事会。[56]然如前论,于增资决议权的配置层面,我们还须同时考虑股东权责维度上的代理成本问题,如此,当如何平衡董事会经营权与股东会控制权?对此,《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与《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的规定殊值参考,即董事会的股票发行决议权应受公司章程限制,而股东会则可通过公司章程限制董事会的权限,以控制其代理成本。[57]
反观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其将增资、减资决议权皆列属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规定与《德国股份法》(AktG)之规定相同,[58]二者皆在一定程度上皆忽视了董事会经营权。如此,我国《公司法》应作调整,立足我国目前实行的资本制度,笔者认为仅需将增资决议权配置于股东会,并允许股东会在保留增资上限决议权的基础上通过“X”将增资决议权进一步让渡于董事会,而减资决议权则无须保留于股东会。
(4)对董事、监事选举权之考量。由股东会选举董事和监事是公司权力纵向分配的第一步,亦是控制代理成本的关键环节,即股东通过行使选举权保障董事会行使经营权与监事会行使监督权的股东导向性,此权犹如高悬董事、监事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若其未能尽忠实勤勉之职,即有撤换之虞,因此,股东会保有董事、监事选举权可极大缩减代理成本。[59]此观点于我国《公司法》、《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以及《德国股份法》(AktG)中均有体现。[60]
值得探讨的是,为了确保公司经营的稳定和持续,股东会可否将董事、监事选举权进一步配置于董事会?于此,很容易得出以下的观点:将监事选举权交由董事会行使会使得监事会彻底丧失对董事的监督能力,由此,监事会即会嬗变成为协助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的机构;而将董事选举权交由董事会自己行使则会更直接地增加公司的代理成本。[61]但笔者认为,此并非考量董事、监事选举权再配置问题的关键,此问题的关键在于允许此权的再配置是否符合效率目标,以及对股东的协商基础进行了必要审视。具体而言,原则上,公司法不应禁止股东通过意思自治对公司权力进行再配置,正如前文所论,股东意思自治虽不一定带来效率,但此应被视为为实现效率目标而做出的努力,具有正当性;但是,于标准公司而言,股东间的协商基础较差,股东会对董事、监事选举权的下放往往利益于董事,以及董事背后的实际控制人或股东,当股东间利益由此失衡或董事会巨大道德风险由此而生时,股东会往往又无法矫正这些问题,即协商基础较差的股东会无法通过“X”使得选举权力复归,从而使代理成本难以得到控制,使公司难以回归效率目标。因此,标准公司的董事、监事选举权乃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
(5)对分红决议权之考量。分红决议权之配置同样涉及股东控制权与董事经营权两个维度,即分红决议乃是股东行使利润分配请求权之前提,此关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直接重要利益,若将此权配置于董事会,似有董事会或董事会控制者[62]利用分红决议权反制全体股东之虞,代理成本极大,如此,分红决议权似应归于股东会;同时,分红决议亦关乎公司运营之财源,从而影响公司的经营策略,如此,是否分红,以及分红的数额、方式等又似属董事会经营判断范畴。[63]两观点针锋相对,于立法例上皆有反映,即我国《公司法》和《德国股份法》(AktG)将分红决议权配置于股东大会,[64]而《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则将分红决议权归于董事会,但公司章程可对其进行限制。[65]
综此两种观点,笔者认为仍应回归公司的效率目标与股东的协商基础考量分红决议权之配置。具体而言,公司的效率目标最终指向者乃是公司的营利性,即公司以取得利润并分配给股东为目的,故分红是目的,经营则是手段,将分红决议权完全置于董事会经营判断范畴而罔顾股东之分红利益乃是手段与目的之错置;但同时,我们亦不可忽视标准公司合理的分红方案有赖于专业管理人才的商业计算,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将分红决议权配置于股东会的同时,应允许股东通过“X”将分红决议权完全或附条件地配置于董事会,由于此权还可通过股东自治复归股东会,故此间所产生的代理成本股东可以承受。于此,似有疑问,标准公司的协商基础是否亦会导致分红决议权无法复归股东会?于前文所论之董事、监事选举权配置中,笔者曾言类似疑虑。对此,笔者认为对分红决议权的配置不同于对董事、监事选举权的配置,因为此关乎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取得分红这一直接重要利益,这会极大缓解标准公司股东冷漠之情,从而使得协商基础极大改善。
(6)对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之考量。公司资产处分在一般意义上应属董事会经营判断之范畴,但公司重大资产的处分则关乎公司的存在以及存在的形式,其与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同属公司重大变更,甚至在美国法实践中,公司分立往往是通过重大资产处分完成的,[66]因此,重大资产处分决议已非董事会独断范畴,基于对代理成本的积极与消极控制,此权应归于股东会,于此,前论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考量部分中已有具体讨论,笔者不再赘述。
上述观点在《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与《德国股份法》(AktG)中皆有明确体现,[67]但我国《公司法》的规定却似是而非,即其第一百零四条规定:“本法和公司章程规定公司转让、受让重大资产或者对外提供担保等事项必须经股东大会作出决议的,董事会应当及时召集股东大会会议,由股东大会就上述事项进行表决。”如此,若公司章程对此只字未提,法律亦无其他规定,是否就意味着公司重大资产处分可由董事会及董事会领导下的管理层独立决议?笔者对此不无疑虑。因此,我国《公司法》应明确将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配置于股东会。[68]
综上讨论,在标准公司中,法律应将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决议权;董事、监事选举权;分红决议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配置于股东会;其中,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上限决议权;董事、监事选举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是“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
至此,标准公司权力配置边界的一侧即已得出,然另一侧,即“董事会经营权是否可通过‘X’配置于股东会”的问题还需讨论。笔者认为,公司的经营应体现出更大的灵活性,立法者应当尊重公司对经营权的自治性安排,因此,法律不应禁止通过‘X’将董事会经营权配置于股东会的行为。然于此可能存在疑虑是,标准公司股东协商基础较差,经营权的上移会不会导致公司经营与效率目标的偏移?对此,笔者欲作三点回应:第一,较差的协商基础确实可能会导致公司经营效率的减损,但上移的经营权并非不可再通过“X”复归于董事会,即以“X”配置经营权是经营灵活性的保障,同时,也是经营效率性的重要纠偏机制。第二,在存在纠偏机制的前提下,法律不应恣意干涉经营权的自治性配置,因为这是股东通过协商所作出的自由选择,即使在此等协商中有相当部分股东的态度是冷漠的,其合意并不充分。因为,对于冷漠的股东而言,将经营权上移至股东会即相当于将公司的经营权从公司的董事会转移至股东会的控制者[69]手中,于此,公司经营权的不同配置并不会减损公司原有的效率,即具体的经营决策或由股东会控制者作出,或由股东会控制者所选派之董事作出,从实践层面上而言,此等差别并不大。第三,事实上,通过“X”对董事会经营权的适当限制一定程度上还有利于董事会及管理层的代理成本的控制。因此,笔者认为,公司法应将公司经营权配置于董事会,但不应禁止通过‘X’将董事会经营权再分配于股东会的行为。至此,标准公司权力配置边界既已完全得出。
2.封闭公司的权力配置边界。封闭公司的经营形态不同于标准公司,其所有权和管理权高度合一。封闭公司的股东人数较少,且其彼此之间往往具有信赖关系,因此,封闭公司具备较好的协商基础,而此等协商基础则是封闭公司可由股东直接管理的必要条件。[70]如此,封闭公司本初的经营中心在股东会,一切公司权力的起点亦在股东会,对此,邓峰教授从公共性的维度重述了此观点,即公共性程度较小公司是股东寻求商业利益的“工具”而非“实体”,[71]本文所言“封闭公司”当属其指;因此,董事会往往是股东会的附庸,其权力之多寡应取决于股东会权力之让渡,如此,股东会似乎可以选择不向董事会让渡任何权力,甚至可以取消董事会,此观点不仅于《美国封闭公司示范补充规定》(MSCCS)、《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中可得到支持,[72]于《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GmbHG)中体现更甚,即依据该法,有限公司不设董事会,而仅设履行执行职责的一名或数名业务执行人。[73]
那么,封闭公司股东是否还可以反其道行之,将本属于股东会的权力让渡于董事会?基于封闭公司股东会与董事会之关系,笔者认为,除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外的余权皆可让渡于董事会。因此,封闭公司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范围即是其权力配置的边界。
前文有论,标准公司的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范围是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上限决议权;董事、监事选举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那么,相较于此,封闭公司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范围将发生何种变化?对此,笔者认为标准公司与封闭公司在协商基础上的差异是导致其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范围差异的决定因素,换言之,当协商基础这一因素发生了变化,原本置于标准公司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范围中的某些权力将被“释放”。在此,回观前论,我们即不难发现惟董事、监事选举权是因标准公司较差的协商基础而被禁止让渡的,如此,在封闭公司中,董事、监事选举权即可让渡于董事会中。[74] 至此,封闭公司权力配置边界亦已得出,即法律应将一切权力配置于股东会,而股东会可将除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上限决议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以外的余权可让渡于董事会。
(二)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
所谓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即公司进行权力配置之自治手段,其范围是什么?公司章程作为公司自治之最高效力文件,涵纳其中,自是无疑;然公司章程以外的何者形式亦可归入其中?即股东决议,股东协议可否归入其中?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径行董事会权力的行为可否归入其中?对此,笔者仍欲以标准公司与封闭公司作分类而讨论之。
1.标准公司的权力配置形式。先论股东协议,学界虽有将公司章程与之视同的论说,但二者之别依然会使以股东协议进行公司权力配置存有障碍,即具有相对性的股东协议似不能拘束作为独立主体的公司,[75]同时,股东协议的缔结未有置备公司之要求,故其对不知情入股者的拘束力似亦有疑。对此,即使是对以股东协议进行权力配置持允许态度的《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其态度亦极为谨慎,不得不对此两大问题进行回应,即股东协议应经全体股东同意,并列入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或章程细则(Bylaws)中,或以全体股东签署的书面方式呈现,并为公司所知晓;同时,该协议应当披露于股票证书或公司给予购股者的书面陈述上,而制定协议前就已在外流通的股票证书则应被召回,并以符合披露要求的股票证书替代;若购股者在购股时不知道该协议的存在,即拥有撤销股权转让合同之权利。[76]此规定虽一定程度上化解了股东协议配置公司权力的法律障碍,但其所要求的协商基础是标准公司难以具备的,换言之,标准公司中股东一致合意的成本巨大,股东协议不宜作为标准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于此,《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的官方评注(Official Comment)特别指出股东协议多被用于封闭公司中。
再论股东决议,其与公司章程虽皆为股东团体意思之载体,但其背后的协商基础却存有极大差异,即公司章程作为公司的“根本大法”,其制定或修订的“形式感”可以极大缓解标准公司股东冷漠的问题;但股东决议其所呈现出的“形式感”则较弱,标准公司的协商基础较差的问题依旧突显,如此,对于公司权力配置这一关涉公司治理结构及其权力运行方式的根本问题而言,股东决议作为权力配置形式似显正当性不足,如积极股东极易利用此等“弱形式”掩盖公司权力配置利己损他的事实。
循此逻辑继续推演,股东会以特别决议的形式径行董事会权力亦不应被允许。因为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的形式径行董事会权力的行为实质上是在改变公司的权力配置,于此,仍存在“弱形式”所带来的协商基础较差的问题。当然,股东会若对董事会不满,其可以动用董事选举权,甚至章程修改权来贯彻自己的意志;股东若认为董事会决议违反法律或公司章程,其可以诉请法院撤销;股东若认为董事违反法律、公司章程、信义义务,其可提起派生之诉,这些行为皆为法律所允许,因为其并不改变既有的公司权力配置。
2.封闭公司的权力配置形式。对于封闭公司而言,其具备较好的协商基础,股东会是公司的本初经营中心和权力起点,董事会乃股东会之附庸。如此,封闭公司股东利用股东决议、股东协议,以及通过股东会特别决议径行董事会权力的行为配置公司权力不存在标准公司中的障碍;惟值探讨的是,股东协议对公司的拘束力,以及不知情者入股公司对股东决议或股东协议所作之权力配置的影响两大问题,详论如下:
(1)股东协议对公司的拘束力。诚如前论,股东协议具有相对性,于合同法层面上,其对公司并无拘束力,但将此等观点置于公司法层面上,则仍有探讨余地。在封闭公司当中,公司章程、股东决议与经全体股东一致合意并置备于公司的股东协议皆为作为公司最高权力执掌者的股东团体之意思,三者的差别仅存在于形式之上,而且从协商基础的角度讲,该股东协议还体现了更充分的合意,如此,若排除此等协议对公司的拘束力似有不妥,也使得封闭公司丧失了应有的灵活性。因此,为化解合同法层面上的障碍,笔者建议,法律应将经全体股东一致合意并置备于公司的封闭公司权力配置协议拟制为公司决议,从而使之具有对公司之拘束力。
(2)不知情者入股公司对股东决议或股东协议所作之权力配置的影响。若新加入的股东在订立股权受让协议或出资协议时对配置公司权力的既存股东决议或股东协议不知晓,该决议或协议是否对新股东不产生拘束力?若如此,公司的权力运行即走向混乱;但若对新股东产生拘束力,似乎亦有侵犯股东知情权而使之相应预期落空之虞,此确为两难之题。
对此,《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7.32条的规定可值借鉴,即股东决议或股东协议所作之权力配置不因不知情者入股而发生改变,其对新股东依然具有拘束力;而新股东若不接受此等权力配置安排,其可于除斥期间内援引重大误解,甚至受欺诈的理据请求撤销股权受让协议或出资协议,并请求相对方承担缔约过失责任。
如此,公司权力配置的形式既已得出,即标准公司权力配置形式仅限于公司章程;而封闭公司权力配置形式包括公司章程、股东决议、经全体股东一致合意并置备于公司的股东协议,以及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径行董事会权力的行为。
五、结论
至此,公司权力配置图景得以重构。具体而言,在标准公司中,《公司法》应首先确立公司所有权力皆归于董事会或在董事会授权下行使的原则;在此原则之外,通过“本法另有规定”将股东会权力与监事会权力划出,其中,将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决议权、董事、监事选举权、分红决议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配置于股东会;于此,《公司法》应允许且仅允许通过“公司章程另有规定”进行公司权力再配置,但是股东会不可让渡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上限决议权、董事、监事选举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也不可以特别决议方式径行董事会权力。而在封闭公司中,《公司法》应将公司所有权力首先配置于股东会;于此,《公司法》应允许股东通过公司章程、股东决议、经全体股东一致合意并置备于公司的股东协议将除公司章程修改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增资上限决议权、重大资产处分决议权以外的余权让渡于董事会,同时,也应允许股东会通过特别决议径行董事会权力。如此,公司权力配置之疑既得回应。值此《公司法》修改讨论之际,笔者希冀本文可资供立法机关与学界批评、研究。
(作者系厦门大学嘉庚学院副教授、法学专业主任)
注释:
[1] 受篇幅之限,本文欲着眼于股东会和董事会分权问题,而这也是公司权力配置问题的核心问题和难点问题,故选此为视角进行阐论则可打通整个公司权力配置问题之脉路,此于董事会与经理等高管之分权问题,甚至监事会之地位与权力配置问题的探讨皆有至关重要之意义。
为简洁行文,本文所谓“公司权力”乃指股东会、董事会职权;本文所谓“公司权力配置”乃指股东会和董事会之分权;本文不再区分股东会与股东大会统一称为“股东会”。
[2] 袁敏、潘晖、彭玲、姜玉霞与黄启人、黄薇、舒韬、仲智中、徐幼明、雅安珠峰商贸有限责任公司损害公司利益责任纠纷案,详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书。
[3]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书。
[4] 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6)川民终950号民事判决书。
[5] 详见虞政平:《公司法案例教学》(第2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18年版,第1308-1309页。
[6] 徐丽霞与安顺绿洲报业宾馆有限公司、第三人贵州黔中报业发展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详见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
[7] 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黔高民商终字第61号民事判决书。
[8] 莫全富与姜彭年、上海申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决议侵害股东权纠纷案,详见王军:《中国公司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61-263页。
[9] 王军:《中国公司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262页。
[10] 杜玉春、熊英和北京恒通冠辉投资有限公司公司决议效力确认纠纷案,详见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11] 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6)京01民终6676号民事判决书。
[12] 《公司法》第三十七条第一款 股东会行使下列职权:
(一)决定公司的经营方针和投资计划;
(二)选举和更换非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监事,决定有关董事、监事的报酬事项;
(三)审议批准董事会的报告;
(四)审议批准监事会或者监事的报告;
(五)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六)审议批准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七)对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作出决议;
(八)对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
(九)对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清算或者变更公司形式作出决议;
(十)修改公司章程;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第四十六条 董事会对股东会负责,行使下列职权:
(一)召集股东会会议,并向股东会报告工作;
(二)执行股东会的决议;
(三)决定公司的经营计划和投资方案;
(四)制订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
(五)制订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
(六)制订公司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以及发行公司债券的方案;
(七)制订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方案;
(八)决定公司内部管理机构的设置;
(九)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经理及其报酬事项,并根据经理的提名决定聘任或者解聘公司副经理、财务负责人及其报酬事项;
(十)制定公司的基本管理制度;
(十一)公司章程规定的其他职权。
[13]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第一条所述之制定目的,第十四条的规定乃着眼于提升公司治理水平,而非特别的监管考量,因此,该条文虽出自于监管规范,但依然可反映出证监会对《公司法》权力配置条款性质的理解。
[14] 参见刘俊海:《现代公司法》(第3版),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585页;杨狄:《股东会与董事会职权分野的管制与自治——以公司章程在公司分权中的地位和作用为视角》,载《财经理论与实践》2013年第11期。
[15] 赵旭东:《公司法修订中的公司治理制度革新》,载《中国法律评论》2020年第3期。
[16]《公司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 股东会会议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代表三分之二以上表决权的股东通过。
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 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过半数通过。但是,股东大会作出修改公司章程、增加或者减少注册资本的决议,以及公司合并、分立、解散或者变更公司形式的决议,必须经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17] 参见王爱军:《论公司章程的法律性质》,载《山东社会科学》2007年第7期;吴飞飞:《论公司章程的决议属性及其效力认定规则》,载《法制与社会发展》2016年第1期。
[18] 邓峰:《代议制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4-59页。
[19] 邓峰:《代议制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9页。
[20] 施天涛:《公司法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15页。
[21] 邓峰:《普通公司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64页。
[22] 邓峰:《代议制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55-66页。
[23] 参见邓峰:《代议制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施天涛:《公司治理中的宪制主义》,载《中国法律评论》2018年第4期。
See Stephen Bottomley, The Constitutional Corporation: Rethinking Corporate Governance, Ashgate Publishing Limited 2007.
[24] 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浙02民终351号民事判决书。
[25] See Jessen, Meckling, Theory of the firm: Managerial behavior, agency costs and ownership structure, 3 Journal of Financial Economics 305, 310-311 (1976).
[26] See Williamson, Transaction-Cost Economics: The Governance of Contractual Relations, 22 Journal of Law and Economics 233, 233-261 (1979).
[27] See Jessen, Organizatio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58 The Accounting Review 319, 319-339 (1983).
[28] 详见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3页。
[29] [美]伊斯特布鲁克、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中译本第2版),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34页。
[30] See Dodd, For Whom are Corporate Managers Trustee?, 45 Harvard Law Review 1145, 1145-1163 (1932); Berle, Corporate Powers as Powers in Trust, 44 Harvard Law Review 1049, 1049-1074 (1931).
[31] 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1页。
[32]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页。
[33] 邓峰:《代议制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61页。
[34] 仲继银:《董事会与公司治理》(第3版),企业管理出版社2018年版,第7页。
[35]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6-112页。
[36]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1页。
[37] 需要说明的是,“封闭公司”(close corporation或close company)之称多见于英美法系语境之中,与之的对应概念为“开放公司”(public corporation或public company);但“开放公司”于我国语境下易引人误解,即将“开放公司”当作“公众公司”而牵涉股份公开发行等问题,故笔者名之“标准公司”以消除此等歧义。同时,我国《公司法》语境下公司的法定分类为“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对此学界多有疑议,即以“资本总额是否划分为金额相等的股份”作为公司分类依据并不能呈现出“有限公司”与“股份公司”在经营、治理等本质方面上的差异;然事实上,在具体的法律调整中,我国法律亦立足于有限公司“封闭性”与股份公司“开放性”的差异上,因此,将公司划分以“标准公司”与“封闭公司”两大形式来讨论公司权力配置问题对我国具有重要意义。参见施天涛:《公司法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60-61页;朱锦清:《公司法学(上)》,清华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6-17页;王军:《中国公司法》(第2版),高等教育出版社2017年版,第6页。
[38] 郭富青:《当今世界性公司法现代化改革:竞争·趋同·融合》,载《比较法研究》第2008年第5期。
[39] 本文所引《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是2016年的最新修订版。
[40] 本文所引《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是指《特拉华州法典》(The Delaware Code)第八编,该法典最新修订于2019年6月7日。
[41] 本文所引《德国股份法》(AktG)参考胡晓静、杨代雄译:《德国商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4版。
[42] 本文所引《德国改组法》(UmwG)参考杜景林、卢堪译:《德国股份法、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德国公司改组法、德国参与决定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
[43] 本文所引《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GmbHG)参考胡晓静、杨代雄译:《德国商事公司法》,法律出版社2014版。
[44] 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45] 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46] 参见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47] 参见郑志刚、许荣、徐向江、赵锡军:《公司章程条款的设立、法律对投资者权力保护和公司治理——基于我国A股上市公司的证据》,载《管理世界》2011年第7期。
[48] 参见《德国股份法》(AktG)第第179条第(1)款。
[49] 《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与《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所规定的公司章程应由“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与“章程细则”(Bylaws)两部分构成,其中,“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是向州务卿报送的注册文件,而“章程细则”(Bylaws)则是根据“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制定的关乎公司治理的运作规则。根据《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10.03条和《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第242条第(b)款的规定,“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的修改首先应经过董事会同意,再递交股东会批准;至于“章程细则”(Bylaws),根据《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10.20条和《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第109条的规定,股东会和董事会则皆有权力修改之。
[50] 根据《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第10.20条规定,股东会和董事会虽皆有权力修改“章程细则”(Bylaws),但董事会相应修改权限可被“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限制,亦可被股东会限制,即股东会在修改、废除或通过一项“章程细则”(Bylaws)条款时,有权明确禁止董事会对该项“章程细则”(Bylaws)条款修改、废除或重述;而根据《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第109条规定,“章程细则”(Bylaws)之修改不得与“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相抵触,此修改权自公司收到任何一笔股款时即归于股东会,而董事会只有经“章程大纲”(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授权时才可享该修改权,但不得以此限制股东会之修改权。
[51] 参见[美]伊斯特布鲁克、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中译本第2版),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
[52] 相较于董事选举权,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涉及股东切身重大利益,此极大缓解了标准公司股东冷漠的问题,可使较差之协商基础得以改进,因此,股东通过公司合并、分立、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控制代理成本效果甚至会优于直接行使董事选举权。
详见[美]伊斯特布鲁克、费希尔:《公司法的经济结构》(中译本第2版),罗培新、张建伟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79-80页;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53] 参见我国《公司法》第一百零三条第二款;《德国改组法》(UmwG)第13条、第36条、第128条、135条、第193条;《德国股份法》(AktG)第262条第(1)款。
[54] 相较我国《公司法》与德国法,《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和《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亦有差异,即二者对合并、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配置的规定与“章程大纲”(Articles of Incorporation/ Certificate of Incorporation)修改权配置的规定相同,议案应首先经过董事会同意,再递交股东会批准。于此,美国法虽赋予董事会更大的权力,但其并未将合并、解散、变更形式决议权完全配置于董事会,股东会对此等议案仍享受最终批准权。同时,《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第275条第(c)款在上述规定基础上又进一步强化了全体股东解散公司之权,即当所有有表决权的股东以书面形式表示同意并按规定向州务卿提交解散证明书备案,也可以授权公司解散,而无需经董事会同意的前置程序。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和《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未对公司分立进行明确规定;但在商业实践中,公司往往通过资产处分等行为实现事实上的分立效果,如此,美国公司“分立决议权”的配置问题即转化为公司资产处分决议权的配置问题,此将在后文中进行探讨。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1.04、9.32、14.02条以及《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51(b)条、第 251(c)条、第266(b)条,第275(a)条, 第275(b)条、第275(c)条。
[55] 参见刘燕:《公司法资本制度改革的逻辑与路径——基于商业实践视角的观察》,载《法学研究》2014年第5期。
[56] 参见潘林:《股份回购中资本规制的展开——基于董事会中心主义的考察》,载《法商研究》2020年第4期。
[57] 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6.01条和第 6.21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51条、第152,和第161条.
[58] 《德国股份法》(AktG)第182条、第222条。
[59] 罗培新:《股东会与董事会权力构造论:以合同为进路的分析》,载《政治与法律》2016年第2期。
[60] 详见我国《公司法》第九十九条、三十七条;《德国股份法》(AktG)第101条第(1)款、第84条第(1)款。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7.28条和第8.03(c)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11条和第216条。值得说明的是,由于《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与《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中的公司治理结构中没有监事会,故不存在选举监事权力的考量问题;而《德国股份法》(AktG)的公司治理结构是双重委员会治理结构,即由股东会选举监事会,再由监事会选举董事会,如此,《德国股份法》(AktG)也确认了选举董事、监事权力乃股东会底股东会不可让渡之权的观点。
[61]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94-196页。
[62] 在标准公司中,董事会的控制者往往是实际控制人、控股股东等。
[63]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75页。
[64] 参见《公司法》第九十九条;《德国股份法》第174条第(1)款。值得注意的是,从我国《公司法》的表述上看,我国《公司法》似将分红决议权界定为股东会和董事会的共享权,即先由董事会制定利润分配方案,再由股东会负责对该方案进行审议和批准。但笔者认为此观点并不周延,从解释论角度看,董事会不将利润分配方案作为议案提交股东会并不意味着股东会无权决议分红,倘若某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三以上股份的股东将其制定利润分配方案作为临时提案提交股东会,于此,股东大会依然有权审议和批准,且董事会基于执行股东会决议职权有义务执行股东会批准分红的决议。因此,笔者认为我国《公司法》中的分红决议权非为股东会和董事会共享权,其仍完全归于股东会。
[65] 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6.40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170(a)条。
[66] 详见施天涛:《公司法论》(第4版),法律出版社2018年版,第546页。
[67] 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2.02(a)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71(a)条;《德国股份法》第179a条。
[68] 在具体的立法中,《公司法》还应明确“重大资产处分”的定义。于此,《美国商事公司示范法》(MBCA)给出的定义是“使公司无法持续实质商业活动的出售、出租、交换或者其他资产处分”;《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Del. GCL)给出的定义是“公司资产的全部或实质性的全部的出售、出租或交换”;《德国股份法》(AktG)给出的定义是“公司的全部资产转让”,同时,将“公司实质性部分资产的转让”纳入“未明文规定之股东会职权”范围。此皆可作为参考。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12.02(a)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271(a)条。
[69] 此处的股东会控制者指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
[70] 罗培新:《公司法的合同解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1-92页。
[71] 邓峰:《代议制公司——中国公司治理中的权力和责任》,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04页。
[72]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21条;《特拉华州普通公司法》第351条。
[73] 参见《德国有限责任公司法》(GmbHG)第6条。
[74] 监事选举权若发生此等让渡,监事会即会嬗变成为协助董事会监督管理层的机构。
[75] 参见蔡元庆、黄海燕:《股东协议治理:缘起、困境与规范进路》,载《财经法学》2019年第2期。
[76] 参见《美国示范商事公司法》第8.01条、第7.32条。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扫描下方二维码进入沙龙分享群。

非常感谢您的报名,请您点击下方链接保存课件。
点击下载金融科技大讲堂课件本文系未央网专栏作者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为作者授权未央网发表,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网站观点,未经许可严禁转载,违者必究!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本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首图来自图虫创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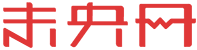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
京公网安备 11010802035947号